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,是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的几个关键节点之一。这一次财政体制的重大变革,对我国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行为有深远的影响,进而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走向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的《以利为利》,用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和翔实的调研案例,对分税制改革的前因后果作了细致、清楚的梳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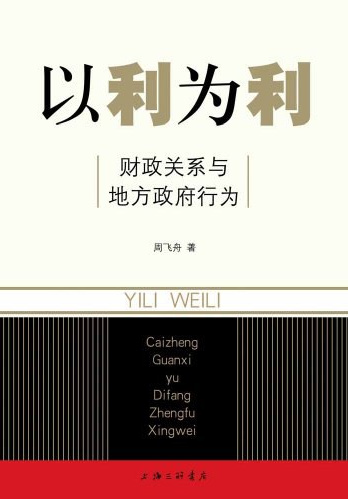
《 以利为利: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》作 者: 周飞舟出版社: 上海三联书店
#1
分税制前的财政包干制推动了工业化
在分税制之前,我国在财政上实行的是“包干制”。财政包干制的具体形式几经演变,各省(区市)之间也有不小的差异,但总体来说,这是一种在财政上分权的体制,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财力和控制资源的能力。以广东曾经实施过的“大包干”制度为例:在每年的财政收入中,广东只需要上缴一个“基数” 给中央,超出基数的部分100%留在广东。
这种“财政承包”的思路,今天看来有些令人不可思议,但放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中,则显得并不违和。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农村的“大包干”,农民们“交够了国家的,留够了集体的,最后都是自己的”,生产积极性一下子提高了。有农村的成功案例在前,承包制又被引入企业管理中。在当时,承包制如此受青睐,一大原因是它符合渐进式改革的思路:在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,依然可以调动生产积极性。在这种“无所不包”的氛围里,财政包干制的引入就显得顺理成章了。
财政包干制制度确实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。在财政包干制下,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辖区内的经济增长是同步的。地方政府只要大办企业、办大企业,就能获得滚滚财源,因此与辖区内的企业,尤其是地方国企和乡镇企业,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。80年代,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是农村改革过程中“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”(邓小平语),也是我国快速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。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,离不开地方政府在金融、财政乃至政治上的支持。
#2
财政包干制下,中央过“紧日子”
财政包干制在推动我国快速工业化的同时,所引发的问题也很快显现出来。首先,在财政包干制下,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,地方政府财力的增长往往要快于中央的财政收入。这导致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,从1984年的42%下降到1993年的22%。其次,由于和本地企业结成了利益同盟, 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“放水养鱼”,藏富于企,在权限范围内为本地企业减税让利。同时,为了少向中央上缴财政,许多地方选择了“闷声大发财”,隐瞒财政收入的做法相当普遍。于是,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,从1979年的28%下降到1993年的13%。
这就是当时引发了大量讨论的“两个比重”下降现象。这两个下降叠加在一起,结果是中央要花钱的地方很多,钱袋子却鼓得不够快。中央财政捉襟见肘,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财政转移凑不出资金,铁路、港口、民航等重点建设项目被卡了脖子,连一些中央机关都要借钱才能发工资,发生过中央向地方“借钱” 并借而不还的事。长此以往,中央的政治权威就可能会受影响。这是中央下决心推行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原因。
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,财政包干制也确实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。一个广为人知的问题是,包干制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,因为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搞“地方保护”,对其他地区的产品设置贸易壁垒。另一个问题是,地方政府扶持和兴办的企业,也存在所谓的“软预算约束”问题,有重视规模扩张、轻视企业效益的倾向。
此外,可能不为大家所熟知的是,财政包干制与当时的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有很大关系。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,中国经济一直存在周期性的大起大落问题。在经济增速超过两位数的年份,通货膨胀率也高达百分之十几。不久,经济增速和通胀率就双双下滑,进入低速增长期,峰谷之间的转换很快。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周期,背后有对应的政治经济学解释。洛伦·勃兰特(Loren Brandt)和朱晓冬的研究,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。
随着乡镇企业等的兴起,国有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的劣势就更明显了。由于国企效益不好,中央要维持国企的就业增长和投资,就需要给国企“输血”。这不外乎有三个办法:第一,直接的财政支持;第二,通过国有银行输送信贷;第三,增加货币投放。
第一个办法,因为财政包干制下中央财政紧张,不灵了。第二个办法,随着改革的推进,银行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:虽然政策上要求信贷流向国企,但非国企的效率和投资回报更高。而地方政府也向银行施加影响,尽力为本地区的乡镇企业争取信贷。因此,国有银行或者直接通过分支机构,或者间接通过城市、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,向乡镇企业输送信贷。在通货膨胀率不高的时候,中央对这些做法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问题是,国有企业怎么办?于是只能使用第三个办法,增加货币投放。很自然地,通货膨胀率也就跟着起来了。
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,中央开始收紧对银行系统的控制。于是,流向非国企的信贷开始下降,货币增发也会下降。然而,由于非国企本身是经济中更有活力的部分,信贷配给的变化也意味着总体经济效率的下降,因此,经济增长速度随着通货膨胀率一起下降了。财政分权导致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, 最主要的体现大概是在这里。
需要指出的是,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是分权或地方竞争本身所带来的,而是渐进式改革常常遇到的困境:经济的某些部分已经得到了改革,而另一些部分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,两者便容易出现结构性的冲突。中央政府对国企的“父爱主义”,以及由此带来的“软预算约束”,使得信贷配置偏离了市场原则,才是问题的根源。

#3
分税制顺利推行
像分税制这样影响既深又广的重大制度变革,预想中会遇到许多阻力,但当时推行的过程其实颇为顺利。1993年4月,中央正式决定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,到1994年1月,分税制就正式实行了。核心的原因,是在中国这样有悠久大一统历史的国家,中央在地方面前还是有绝对的政治权威。当然,有些省份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,比如当时经济发展最好、从包干制获益最大的广东省就抬出一柄“尚方宝剑”:“小平视察南方时说,广东要赶‘四小龙’。搞分税制以后,我们就没法赶‘四小龙’了,小平提出的既定目标就实现不了了。” 不过, 这更可能是一种谈判技巧,以换取分税制落实后的更多优惠条件。
当然,朱镕基当时所采取的策略也很重要。他的考虑是先把分税制这个整体制度尽快树立起来,因此要抓住全国统一的分成比例等核心要件,在基数和减免政策等具体问题上,则可以照顾地方利益,用短期让步换取长远的“增量”。事后来看,他的策略相当有效。分税制实施仅一年时间,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就从1993年的22%提高到1994年的56%。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,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速接近20%,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速。因此,“两个比重” 下降的趋势都被扭转了,中央过“紧日子”的阶段过去了。
1994年后,经济的大起大落和间歇性的高通胀问题,也得到了有效控制。这与朱镕基主导的几项重要改革都有关系。
第一,分税制改革大幅提高了中央的财力,因此中央可以用财政而不是货币手段去支持国企,避免了高通胀的出现。
第二,朱镕基主导“抓大放小”的国企改制,使亏损的中小国企或倒闭或改制,政府向国企输血的负担客观上减轻了。
第三,相对不为大家所注意,也是书里没有强调的是,与财政的趋势一致, 当时的银行系统也经历了一个“再集中化”的过程。中央加强了对银行系统的控制,削弱了城市、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与国有银行的联系。然而,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,是让信贷进一步向国企倾斜,不利于提升信贷配置的效率。朱晓冬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。他们发现,1994年之后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实际上在恶化,但这个问题被当时的高速经济增长暂时掩盖了。

#4
分税制后,地方政府过“紧日子”
分税制实施之后,中央切走了财政收入的一大块,于是风水轮流转,轮到地方政府过“紧日子”了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最后花出去的钱少了。在分税制实施后,地方开支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是在上升的。这里的“紧日子”,说的是地方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税收大幅减少了。这深刻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。
分税制首先削弱了地方政府与本地企业之间的联系。分税制实施后,中央拿走了增值税的75%,而增值税又是工业的主要税种,因此地方政府从扶持、兴办本地工业企业中获得的好处大幅下降了。另外,随着银行系统的“再集中化”,乡镇企业等非国企获取信贷的成本大幅上升了。整个20世纪90年代后期,也是曾经辉煌的乡镇企业不断倒闭和改制的时期。这个重要的变化, 对我国的整体经济效率和区域经济发展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,似乎还缺乏深入的定量研究。
前面提到,划归地方的税收大幅下降了,而地方政府的总支出在上升,这中间的差额是由中央向各地的财政转移支付补足的。这看上去似乎与包干制时代没有差别,但问题在于,中央的转移支付大部分是“戴帽”的专项资金,事先规定了专门用途,地方政府花起来很不“自由”。例如,地方政府没有办法用这些专项资金来发工资。在财政资金不断向下流动的过程中,专项资金的比例是扩大的,越到基层反而越高。换句话说,在财政包干制时代,地方政府是“自己收钱自己花”,在分税制时代则是“自己收钱别人(规定你怎么)花”。
专项转移支付的一个优点,是中央能更好地引导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, 这与我国实施分税制的初衷是一致的。但同时,这又造成了一个并不理想的后果,那就是地方政府的眼睛会更多地“往上看”,而不再是“往下看”。加上大部分专项资金是需要地方去争取的,因此“跑项目”“跑部钱进”就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,需要地方投入大量精力、物力。另外,信息在自下而上的流动中会有很大损耗。基层政府最了解基层情况,而中央政府离得最远,这与自上而下分配资金的方式有时候就会产生冲突。
当然,中央政府设计了如此之多的专项转移支付,有另一个不得已的苦衷:如果对转移支付的用途完全不做限制,地方开支的膨胀就会更无节制。官僚系统有难以抑制的扩大规模的倾向。实际上,在地方财力宽裕的包干制时代, 地方的财政供养人员增长很快,到了1993年已经积累了大量“冗员”。进入分税制时代,地方政府的工资拖欠一度成了普遍现象。而大规模的基层工资拖欠,又以中部地区尤为严重。原因在于,东部沿海从对外开放中获益大,工业和经济增长都很快,因此财政状况普遍不错。西部地区则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量转移支付。农业人口众多的中部地区“两头不靠”,因此在财政上最为困难。
既然从工业部门获取税收的路子窄了,地方政府就把“开源”的手伸向了农业和农民,导致农民的税(农业五税)、费(“三提五统”)负担日益加重,并且费的负担要远高于税。这个问题在中部地区尤为突出,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。为此,中央在21世纪初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村费税改革,摊“费”入“税”:取消农业费,部分地提高农业税,并通过转移支付补足地方的收入缺口。此后,中央又逐步降低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。两千多年来,农民们第一次不需要缴纳“皇粮”了。
农村费税改革和农业税的取消,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,那就是农村乡镇一级政府的“悬浮”状态。在此之前,乡镇需要从农民那里征收税费,并以此为基础向农村提供基础教育、水利等公共服务,因此与农业和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。改革后,基础教育等重要事权上收到了县里,而乡镇的经费则主要由上级拨付,于是乡镇一级政府的“眼睛”往哪里看,注意力放在哪里,就不一样了。在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和老龄化的背景下,乡镇还有没有必要维持如此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?农村的公共服务能不能由更加市场化的办法来提供?这些问题,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。

#5
土地财政兴起
分税制改革让地方政府的预算内财政“不好花”了,于是地方政府急切需要开辟“新战场”,寻找新的可支配收入。90年代中后期,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步子加快和房地产的市场化改革,一个巨大的财源出现了,那就是通过出让土地获取收入。很快,以土地收入为中心,地方政府打造了一个规模大、可操控的预算外体系,“第一财政靠工业、第二财政靠土地”,这就是通常所说的“土地财政” 。土地财政的出现,让地方政府暂时摆脱了“紧日子”,也让很多地方的工作重心转向了“经营土地”与“经营城市”。
从理论上推演,能产生大量土地财政的地方,或者是工业化速度很快,或者是有大量人口流入,或者两者兼而有之。但事实上,很多工业化速度并不快的人口流出地,也能把土地财政玩得风生水起。其中的奥秘,就是作者在书中所总结的土地、财政和金融相结合的“三位一体”模式。政府以土地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,然后以抵押贷款进行新一轮土地征收,并用出让土地的收入偿还抵押贷款,如此循环往复。只要财政和金融资金不断投入城市建设,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也会持续增长。于是,土地、金融和财政之间形成了一个互相增强的闭环。
当然,一个地区所能出让的土地,受到当年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制约。陆铭的分析指出,从2003年开始,我国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就开始偏向人口净流出、工业化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。因此,中西部的许多地方在“土地城市化” 的道路上走得更远,建设了许多“远、大”的新城,为此后的巨额地方债务埋下了伏笔。我和钟粤俊、陆铭在《管理世界》上的文章发现,从2003年开始, 中国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,结果城市人口密度反而是下降的。
值得一提的是,给定建设用地指标,地方政府对不同类型的土地,采取了不同的出让策略。其中,工业用地的供应相对充足、出让价格低,商住用地的价格则平均要高出数倍。推想其中的理由,工业企业通常规模更大,在生产网络中也处于更核心的位置,并且在不同地区之间有更高的流动性。因此,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短期内的GDP增长目标,会以低价土地吸引工业企业。这样做的好处是降低了我国工业的生产成本,但代价是居民承受了高昂的房价。于是, 我国工业的相对过剩和总体消费不足就同时出现了。我和陆铭等人的研究表明, 这种做法造成了显著的福利损失。
#6
太阳底下无新事?
这本书讲的事情,对现在的读者来说早已经是历史。在本书最后几章出现的、在当时尚属“新鲜事物”的土地财政,现在也到了逐步退场的时候。但我在读这本书时,感觉这些事仿佛就在眼前。这大概是因为,与当年相比,今天有一些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,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。
对我个人来说,本书最有知识增量的地方反倒是第二章,即改革前的中央-地方关系。读者们可能知道,“增长锦标赛”是解释90年代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理论。尤其是在分税制实施之后,地方政府从本地企业中获取税收的比例大幅下降,为什么它们还有动力去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?增长锦标赛可以提供一种自洽的解释。然而,第二章里提到,在“大跃进”时期,中国已经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锦标赛,结果却是国民经济的大幅倒退和农业上的巨大灾难。如果我们相信后来的锦标赛推动了经济增长,那为什么前面的锦标赛带来的是经济灾难?这中间的区别,值得我们思考。
有心的读者大概注意到了,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央地财政关系有了一些新的提法。要理解这些重要的变化,本书所蕴藏的洞察和智慧是不可缺少的。因此, 对于想要理解中国经济和治理、关心中国未来的读者来说,这本十几年前的书并未过时,它的再版十分应时。
文章来源 | 复旦商业知识
